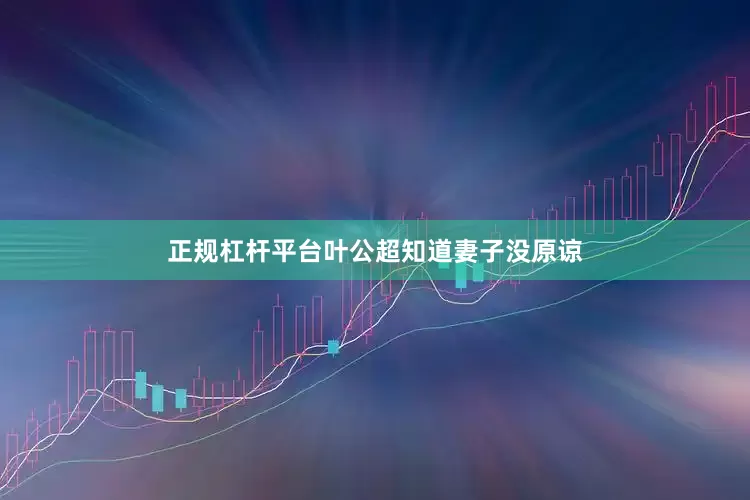
文|徐 来
编辑|徐 来
文|徐 来
编辑|徐 来
《——【·前言·】——》
叶公超,民国外交牌面,风度儒雅、满腹经伦。
可谁能想到,这样一个人物,晚年竟独居孤老,连妻儿都不在身边, 他犯的错,在床榻之间。
“堂妹”风波前,曾是最得体的一对
叶公超出身湖北叶氏望族。家世清白, 早年留学宾夕法尼亚大学,才华横溢。
归国之后,他在燕京大学任教,讲授英文、文学,文风刚健、仪表堂堂,被称为“燕大风流才子”。
袁永熹,是燕大物理系学生,出身学者之家,气质沉静端方,物理、数学样样精通,仪态又出众,是那一届公认的校花。
展开剩余90%两人相识于燕大礼堂,叶公超在讲座,袁永熹坐在台下。
后来互通书信,交往很快定下。
婚礼不张扬,只是学校师生小型茶会,但在当时知识界,是一桩风头极盛的联姻。
一个写英文诗的学者,一个搞量子物理的才女,在那场动荡年代,他们曾是许多人眼中“最登对”的夫妻。
婚后不久,他们育有一子一女。
家中照片还留着:丈夫西装挺括,妻子旗袍素雅,两个孩子站在前头,眼睛炯炯。
那个家庭,是民国留学派理想生活的缩影。
1930年代,局势渐变,战争阴云逼近。为避战火,袁永熹携子女赴美。
叶公超留在国内任职,不久进入中央政治圈,出任驻外大使,先后派往新加坡、泰国、菲律宾,仕途飞升。
此时起,两人开始长期分居,往来靠信件,感情靠记忆维系。
几年之后, 信越来越少,照片越来越旧,孩子已经认不清父亲的脸。
我查过史料,发现1940年代后,袁永熹主动不再回信,传言她在美定居后,已认定这段婚姻维系不了,但没明确离婚。
她说得少,但她做的决定很清楚, 不骂、不争、不等,只是带着两个孩子,在异国他乡重新生活。
那时叶公超在哪?人在南京,官至外交部长。场面体面,人前风光。可家里空着,桌上没人开饭。
外人看他风度不减,仍是谈吐风雅。
可我翻过几篇吴宓的笔记,里面写得很隐晦。只一句:“叶某近日近女眷,堂亲。”
堂亲?查了才知道,是叶崇范,族中堂妹,一度照料叶公超病中生活。
照料到哪一步?文献没明写,但从袁永熹反应看, 她回国探亲时曾直面撞见叶与堂妹同处一屋,从此一别再未联络。
她转身那一下,没吵没闹,直接带两个孩子回了加州。再没联系。
“她没离婚,也没原谅”
袁永熹不离婚,也不再回头,在加州大学任物理研究助理,靠奖学金资助儿子上学。
后来女儿也留在美国成家, 用自己的方式,让孩子过上安稳生活。
她不主动谈过去,熟人问起,也只淡淡一句:“各人自有因果。”
有人说她狠,有人说她忍,我觉得,这种冷淡,是她给出的审判。
叶公超知道妻子没原谅。可他又不敢提离婚。他还写信,还试图寄照片、寄礼物,想让孩子原谅他。
信寄出去没回音,东西退回来了。他手下的人记得,那时他写信都在打草稿,改三四次,才抄清一份。
堂妹一直在他身边。后来两人同住多年,甚至有人说她“以妻相待”。可始终没人敢称她“叶夫人”。
社交场合,叶公超总是一个人。座位边空着,签名册上永远不写配偶名。
他清楚,这段事儿,永远翻不了篇。
1960年代,叶公超赴美访问,想见孩子,女儿没见,儿子答应,只谈了十分钟,全程没有寒暄,也没合影。
走出咖啡馆时,儿子说:“我只认我妈”,我觉得,这句话,比骂人还狠。
晚年,叶公超回台静居,无职、无官,也无家,媒体报道过他的书房,堆满信札与文稿。
他写回忆录,写的是外交谈判、文化交流,却避开私事不提。
有人问他对家庭有何遗憾,他不答,只是沉默,偶尔笑一下,轻声说:“报应。”
这话没录音,几份记录都提过,不同来源、不同版本, 都提到一个关键词——“报应”。
他没喊冤,也没求原谅,他知道,自己没那个资格。
一个人的晚年,一屋子的空椅子
叶公超晚年,住在台北阳明山,房子不大,三室一厅,一间是书房,一间是卧房,还有一间一直空着。
那间空房,没人住,也没人打扫,朋友问他为啥不改书房,他说:“给他们回来住。”
谁?当然是袁永熹和孩子们,可他们再没回来。
整整四十年,没有一个节日、一个电话、一个问候。
他身边还是叶崇范,身份没变,称呼模糊。
有人叫她“堂姊”,有人叫她“女友”,没人叫她“夫人”。
我查阅资料,叶晚年每周一次去台北国立图书馆看旧信,有一次被管理员看到他在翻1937年袁永熹写给他的英文信,那封信他读了三十遍。
信上没责备,也没感情,只是一份例行的生活描述,字里行间,清冷如冰。
朋友都知道他变了,年轻时幽默风趣,后来话越来越少。
他唯一坚持的事,是每年5月去美国驻台协会寄一次信,收件人:Y.Y. Yuan,California。
他不写多,内容固定,问候健康,提起往事,偶尔夹张照片,每次都寄,每次都退,不信命,但看到这些信,他忽然觉得——人这辈子,有些债不是金钱能还的。
1976年,叶公超因脑溢血病倒,入院十天,无人探望。
叶崇范守在病床边,日夜照料,那张病床上的人,临终前只念了一个名字:“永熹。”
说完这两个字,他就没再睁眼。
台北给他办了追悼会,送行者众多,可没有他的家人。
袁永熹没到,孩子们也没发唁电。
追悼文上称他“忠诚外交家”“文化战士”“文人首相”,可我觉得,那些词都不重要。
他真正该面对的,是那个没有回信的地址。
结局未写的信,和一封冷静的挽联
1977年,袁永熹在美国收到讣告。
她没哭。她让人送来一副挽联,署名“Yuan Y.Y.”。挽联很短:
昔人已矣,纸灰难暖。春风未动,旧梦犹寒。
联语在场者一时没懂。后来有人说,“纸灰难暖”是说那堆叶公超写了一辈子的信,烧了也不会带来一丝温度。
“旧梦犹寒”,是她这一生最克制的冷酷。
她没去台北,也没安排子女吊唁。只说:“我与他早已无话。”
她八十岁后身体日衰,住进疗养院,直到1991年离世。葬于加州,墓志上不提夫姓、不列配偶,仅书“物理学者 袁永熹”。
她没留下遗嘱。孩子处理遗物时,在旧书箱中发现几封叶公超寄来的信,未拆封。
我读到这一段,脑中只剩一个词:决绝。
她一生没再婚,也没改变姓氏。但她拒绝被归入任何男人的墓志铭。
你说她狠?她只是从不宽恕。
你说叶公超惨?他只是在结局里为自己写了一份注脚。
一生风光,满纸辉煌,不敌一个女人的背影。
我认为,真正的“报应”,不是别人给的,是自己在失去时意识到自己早该失去。
名利能补偿失眠吗?文字能换回一顿晚饭吗? 你写下再多外交文书,也抵不过当年那句“我只认我妈”。
这桩婚姻,从未彻底终结。但从袁永熹转身那天起,叶公超就再没赢过。
他输给了那个从不争吵、不哭喊、不指责的女人。
那种沉默,比一万个巴掌更响。
发布于:福建省股票配资网站排行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